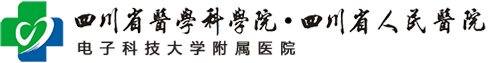2015年第10期第四版
版面选择
知识窗:找证据与讲故事 叙事医学的一片蓝海
2019-04-11
现代临床医学的冷面孔一部分源自“挖地三尺找证据”的思维定势,它的学名叫“循证医学”,肇始于临床思维与公共卫生思维(主要是流行病学)的结合。走出了传统的经验与推理的迷思,由此带来了临床医学的精确化、实证性与前瞻性。但也带来一种新的认知偏颇,那就是漠视客观、观察、实在证据之外的主观、体验、情感的因素,助长了技术主义、客观主义思潮。对此,美国医学界有过清醒的反思和积极地探索,近年来在循证医学的红海之外开辟了一片蓝海,那就是“叙事医学”。
叙事医学的价值就在于纠正这种偏差,寻找新的出路。将“找证据”与“讲故事”结合起来,构成客观与主观、观察与体验、生物与生灵、技术与人道有机地统一起来了,如果说美国医学的前沿只有循证医学,那是对美国医学的误读。可惜,这样的误读在当下还十分盛行。其实,中国哲学有情本位的认知传统,讲究通情达理,入情入理,情理交融。我们更应该接纳、提升新生的叙事医学。
循证医学的开山祖师是英国医生和流行病专家科克伦,他也是一位叙事医学最早的探索者,他的代表作是1972年出版的《疗效与效率》,书中记载了萌生创意的过程。二战期间,他曾作为军医从军服务,不久便被德军俘虏,在战俘营中从事医疗工作。当时战俘营里正流行白喉,而药品又极其缺乏。起初,他估计战俘营将会因白喉流行造成数百人的死亡,但结果却仅有4人因此丧命,而且,其中3人还有枪伤。这件事促使他注意到人所具有的自然康复能力是十分强大的,并由此对医疗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。正是为了消除这种怀疑,他开始倡导并实施临床随机比较试验(RCT)。临床随机比较试验现已成为循证医学的重要方法。
科克伦不仅是循证医学的创始人,也是叙事医学的探索者,战俘营里,某一天,一位年轻的苏联战俘哭泣叫喊不停,一开始他认为是胸膜炎的疼痛引起哭叫,此时,手中连一粒止痛片也没有,绝望中,科克伦本能地坐到患者床上,把士兵抱在自己的怀里。于是,奇迹发生了:士兵停止了喊叫,直至数小时后平静地死去。后来,他认为这个患者不是躯体痛苦而哭叫,而在于孤独而起的精神上的痛苦。由此,他又开始质疑药物治疗对于具有思想与情感的人类疾病的确定性。
叙事医学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学院的临床医学教授卡蓉2001年提出的新名词,主要是探讨文学与医学的关系,研究文学叙事(生命叙事、苦难叙事、衰老叙事、死亡叙事等)能力对于医学认知生命、疾苦、死亡的积极意义。可惜,她的代表作《叙事医学》还没有中译本,最近被译为中文的叙事医学专著有哈佛大学医学院阿瑟?克莱曼的《疾痛的故事:苦难、治愈与人的境况》,克莱曼首先在语义上将“疾病”与“疾痛”区分开来,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,一个是医生的世界,一个是病人的世界;一个是被观察、记录的世界,一个是被体验、叙述的世界;一个是寻找病因与病理指标的客观世界,一个是诉说心理与社会性痛苦经历的主观世界。
然而,现代医学信奉单边主义的“真相大白”,唯机器检测的结论为准绳,在技术主义的喝彩声中一路裸奔。进入这样的临床路径,必然只有病,没有人;只有公共指征,没有个别镜像;只有技术,没有关爱;只有证据,没有故事;只有干预,没有敬畏;只有呵斥,没有沟通;只有救助,没有拯救……就这样,技术与人文疏离了,现代医学迷失了,丢失了仁爱的圣杯,逐渐被技术主义所绑架,被消费主义所裹挟,成为不可爱的医学。
(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 王一方)